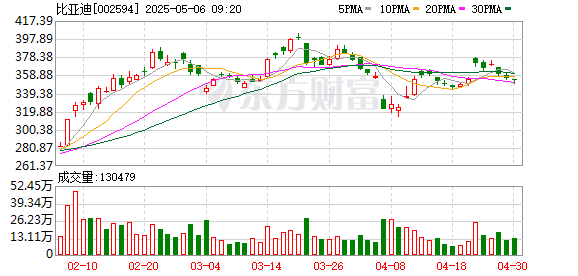服务业打工人配资专业门户,困在表演劳动里
"可以坐着上班"
打开招聘软件,可以看到制造业与服务业不少招聘广告中,正在把"坐着"当做一项工作福利。仿佛"能坐着工作"本身就是一种特殊待遇。
与之相对的,是基层服务行业中日益普遍的"全程站立":餐饮、零售、酒店等岗位的员工,许多都被要求在超长工时里全程站立工作,不设椅子,没有休息,不能坐下。
这种要求并非出于效率或安全考虑,而是源于一种看不见的表演逻辑:站立的身体,被当作"积极""专业""热情"的象征,传递给顾客、传递给管理者,也传递给摄像头背后的监控系统。
"坐着会给顾客懒散的感觉,会让顾客不想进来消费。"一位经营者如此解释。
这是一种和真正的劳动不同的劳动。它的价值不在于完成工作本身,而在于营造出"在工作"的姿态。
"在工作"的劳动姿态,开始被单独抽离出来加以规范。站着、走动、微笑、口播,成为评价绩效的一部分——它们并不直接提升服务效率,却不断被强化、被记录、被奖惩。
当劳动变成表演,劳动者也就成了道具。健康被消耗,情绪被压住,人与人之间的真诚被替换成标准化的笑容和话术。这不仅是服务业的日常,也是当下许多岗位的现实:制度用可复制的动作定义"合格"。
01 口播
在许多门店,劳动的第一要求不是把事情做快,而是把样子摆对。
小光在一家餐饮连锁工作,每天站十个小时,下班回宿舍总是一瘸一拐。去医院问诊,还没拍片,医生光听描述就判断——静脉曲张、腰椎间盘突出、膝关节积液。这些病,在服务业是再常见不过的职业损伤。
要缓解并不难。一双压力袜、一副支撑性鞋垫、每站五十分钟坐十分钟,都能让情况好很多。但店里不允许。
这种逻辑里,站立并不一定能提升效率,却成了"敬业"的证明。于是,哪怕客人不多,员工也不能坐下。前厅留一人值班、其余人去后台休息,这样的安排被认为"不专业"。
表演站立虽然辛苦,但好在不要求技巧,如今的服务业工作中还包含着更多不被认真解释、却必须严格执行的"表演性劳动"。
地上没有垃圾也要扫,不赶时间也必须小跑上菜,上班时要一直走动,遇到同事必须打招呼问好,如果被经理抓到没有笑,会被批评。这些动作不一定改善顾客体验,却能让管理层看到一个忙碌、整齐的场面。

在奶茶店兼职的张章做好了脚疼腿疼的准备,却没想到嗓子成了损耗最大的地方。
兼职第一周,他每天口播到嗓子干哑,吞口水都疼。一位同事辞职了,因为声带结节。
店里有一套细得近乎荒诞的口播 SOP:顾客进店要喊,点单要喊,取餐要喊;天气变了要喊,季节更替要喊。每隔十分钟,全店会齐声高喊"毛巾清洗时间到""三十分钟检查茶汤时间到"。
这些台词里,有提醒顾客小心烫口的好意,也有品牌广告,还有复杂的问候与告别话术。奇怪的是——顾客在的时候要喊,没顾客的时候更要喊。
"你得有活人味!" 店长批评张章的表情僵硬,口播毫无感情。

在张章每天站立的十个小时里,没有一刻是停下来的。他得当后厨,泡茶,泡咖啡,煮珍珠,切水果,滤茶叶,不停地洗洗刷刷,还得看前场,点单,收银,处理线上的订单。
京东美团和阿里外卖大战,订单激增, 上早班的张章一个人干了一千多的营业额,他打电话求助,店长敷衍了几句就不闻不问了。其他同事没到上班时间也不来。张章说他很理解,如果是他也可能会"见死不救",正常上班时长已经让透支了所有体力,大家都没有力气再来赚这一小时十块钱的加班费。

外卖大战期间的奶茶店
没有力气当活人,又要表演口播喊麦,那就只能当伪人。
火锅店在三楼,四楼是健身房,穿着运动装背着运动包的路人显然不是来吃火锅的,但小光仍会笑容满面拦住上楼的路人,推销最新口味的锅底;客人们正聊得投入,小光仍会时不时走上前去打断对话,询问是否需要加水;排了很久队的顾客不停看表,张章知道对方着急,但还是先念完冗长的口播词再让顾客点单。
张章很快学会了用标准微笑对所有人用同样的语气说出同样的话,在高负荷劳动抽走体力前,张章先抽走了自己的感受,不然无法消化路人的冷眼,客人的不耐烦,还有自己的尴尬。
天气很热,穿上品牌的充气服更是进了蒸汽笼,但是张章说他还挺期待上气的,因为这样他就可以不用管理表情,也不用说话,在当充气假人半个小时里,脸可以毫无顾忌地垮下来,像活人疲惫时一样。
02 乐捐
有时取餐的顾客已经走了,店员仍对着空气口播,直到念完。
这些词本来就不是念给顾客听的,而是念给摄像头,店长,或者念给潜伏在顾客队伍里的"便衣"督查。

火锅店里的摄像头
某品牌奶茶店对口播每周有五次随机抽查,四次监控一次线下。
如果被发现没念,便会按照打分标准扣分,不仅可能会被罚写复盘,还和工资提成挂钩。
监控,罚款和体罚是管理的主要手段。
在许多公司,罚款叫 ¨ 乐捐 ¨。
乐捐本是民俗宗教用语,明清时期开始,善男信女为了表示对关帝的敬仰和报答,给关帝庙捐钱。
有的奶茶店,规定收银人员如果面无表情,第一次捐一元,第二次捐两元,以此类推。
某长三角地区的奶茶品牌有门店要求没喊口号的员工"乐捐" 50。
某湘菜品牌上菜时有固定口播,如果服务员没说,罚款 10 元,女员工没有涂口红罚款 5 元。
张章的同事曾一个月被扣了一千多,将近工资的三分之一。
体罚也非常普遍,某连锁咖啡品牌要求店员抄写差评,每条 100 遍,如果没对路过的顾客微笑打招呼便被罚做俯卧撑,其他的体罚比如深蹲、爬楼梯也屡见不鲜。
"总比罚钱好"有人在评论区这么说。
不少顾客抱怨口播。
越来越长的口播词让顾客的等待变得更长了,在循环的口播噪音里,顾客也听不清店员快速念完的营销话术究竟在说什么,消费过程中必要的沟通反而变得困难,一是因为环境太吵,二是有时店员只有力气用机械的话术应对顾客具体的问题,太过疲惫而无暇给出更有效的反应。为了不被罚款,很多店员宁愿打断顾客的询问,也要坚持把口播词念完。
在这样的制度里,笑容不再是热情的自然流露,而是为了避免损失;声音不再是沟通,而是为了在监控画面里显得合格。
这种管理的逻辑简单直接:它几乎不需要额外成本。2024 年,中国城市私营单位员工平均月薪约 5789 元。像小光这样每天站十小时、月休四天的服务员,时薪只有五六元。而一杯奶茶售价十五到二十元,即使成本十元,一小时卖出几杯,就能创造远超员工时薪的现金流。相比投入资金研发新品、升级设备,强制员工喊麦、保持站姿几乎零投入,还能立刻呈现效果。
但这种看似高效的方式,其实是短视的。它让员工疲于维持表面动作,真实的服务效率下降;为了监督这些表演,还需要更多培训和抽查;高流动率又让招聘和培训成本不断增加。最重要的是,它逐步消耗掉那些最能打动顾客的部分——真实的关怀和回应。
03 伪人
公司试图用量化考核制度将一切标准化、流程化,本意是以用户为中心,提供最好的产品和服务。然而,最影响顾客体验的偏偏是那些无法被量化的部分。
管理者无法观测消费者在店员那里获得多少情绪价值,就去要求笑容和声量,在动不动就罚款的威胁下,店员们也渐渐把力气从"做得好"转移到"做得可以好看"。
越来越多的人想要逃离一身班味,想要通过消费要感受活人味的服务。
服务员本来就是活的人,但经营者偏偏用一套标准化 SOP 和严苛罚款把活人僵化抽干成伪人,然后再让伪人死气沉沉地表演活人。
无数人的时间和精力都用来抽干人,再用整无数花活儿来让人表演人,好一个加一减一等于负的集体伪人时代。
更令人担忧的是,这些以劳动者血汗作为代价的冗余并不会这样消散,这其中的不满,恐惧,潜入社会的肌理,进入到弱肉强食的暴力循环。
不摇奶茶还能去哪儿?摆在这些劳动者眼前的只有两条路:进厂,当店员。
工厂打着"坐着上班"的广告吸引着站累了的服务业年轻人,而流水线上,又是一排排必须坐着的人。


强调"坐着上班!"的招聘信息
低门槛劳动者的别无选择让学校里的学生别无选择地卷,不然,"就只能像他们一样。"
基础劳动者的工作状况决定着一个社会的尊严底线。而如此的表演性劳动剥夺的不仅是在岗者的尊严,更剥夺着所有人的安全感。
04 代价
代价首先落在身体上。小光的膝盖和腰椎承受着日复一日的压力,张章的嗓子在不断的高声口播中逐渐失去弹性。静脉曲张、声带结节、慢性腰痛,这些原本属于长期体力劳动者的伤病,如今在大量服务业岗位上提前出现。
更隐蔽的,是情绪的耗竭。为了应付镜头和考核,员工学会了用同一套表情和语调面对所有人,把真实的感受收起来。在这种环境里,正如社会学家霍克希尔德所说,情绪劳动可能导致"情感异化"——劳动者与自己的真实感受逐渐脱节。
我也曾在另一种"表演劳动"中体验过这种耗竭。三年前,我在一所海外中文教育平台做线上老师,一次下课后,学生妈妈试探性地抱怨,说老师怎么每次到了点儿就匆匆地下线走人,在全是外国人的环境里,华人小孩对来自中国的老师特别亲切,每次都期待着多跟老师聊聊。家长还补充,不是想要白白占用老师时间,只是这课上的,也太没有人情味儿了吧。
我很理解家长的意见。没有比课堂更需要人味儿的职业了。
但我没有精力当人。
两节课之间只有十分钟休息,迟到半分钟就要被罚掉半节课费。出镜的光线、镜头的位置、衣服的颜色、妆容,全都被编码进考核数字,然后成为罚款的原因,更别说生病请假了,有一次我突发高烧,当天的课程无法进行,工资没有不说,直接被二倍罚款,相当于十节课白上。
曾经有一个老师食物中毒,但又不愿被高额罚款,只好坚持上课,在桌子下面放了个盆,抽空呕吐。有一次学生在课后想倾诉被同学排挤的经历,我陪她多聊了一分钟,结果当天被罚两百元。这就是"当人的代价"。
劳动原本是人与人之间的连接。但在表演化的劳动里,这种连接被削弱甚至切断,取而代之的是一套冷冰冰的标准。惩戒和监视的管理制造着失去自主性的劳动者,表演式服务生产观光式的消费者,这期间,消失的是人和人之间真正的关切。
 配资专业门户
配资专业门户
明道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